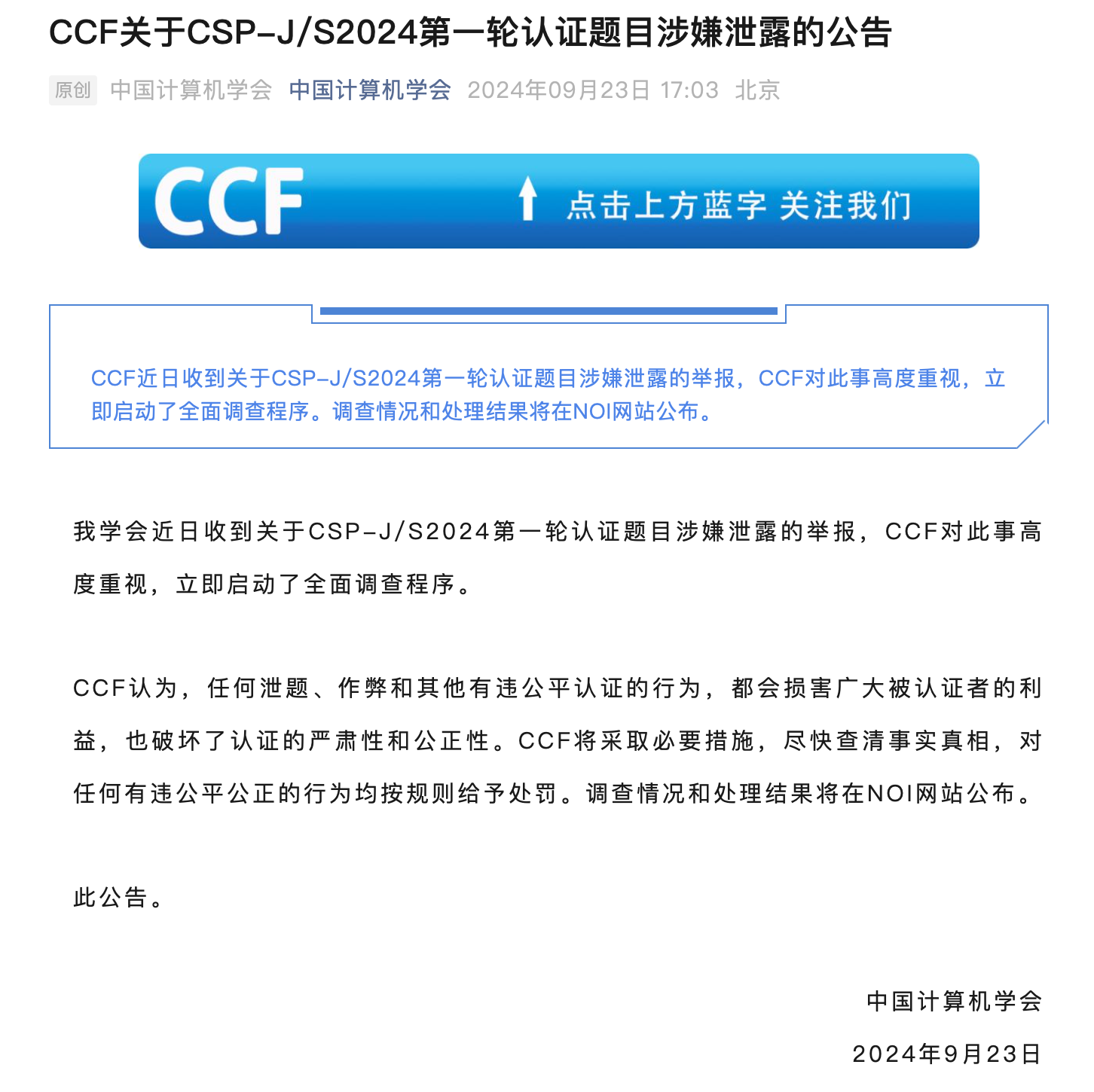2023年12月13日 张能苗
□张能苗
在我小时候,有一位呵护我成长、对我人生有着深刻影响,又颇具几分神秘色彩的人,他叫张顺孝。在我的记忆里,他中等身材,略显清瘦,鼻梁笔挺,慈眉善目,两眸炯炯有神,脸型瘦长尖下巴,看上去和我市的一位先贤颇有几分相似,他年轻时肯定是一个美男子。
按照辈分,他真正高出我四辈。他人生坎坷,刚20岁出头就遭遇了父母双亡,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因为当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娶不起媳妇而打了一辈子的光棍。新中国成立后,他已年近花甲,自然成了我们生产队的一名五保户。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善言辞,却总是爱不释手,老捧着那一把沾满了斑驳浓浓茶迹的旧陶瓷杯,这一度成为了他的标配。同时,他一辈子保持着山里人的淳朴厚重和善良,深受全村人的尊重和爱戴,年长的族人尊称他“顺孝叔”,中年的族人尊称他“顺孝公”。
他对我来说,虽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自从我出生呱呱落地起,他就把我当作了自己嫡亲的后代子孙一样呵护,抱在怀里,爱在心里。
听隔壁阿婆和我母亲说,在我襁褓的时候,他经常一会儿“吱嘎、吱嘎”摇着从我的大姨妈家里借来的那只竹编木架子摇篮,一会儿起身把我抱在怀里,用剪过的一小撮短短胡须剌激我那又白又嫩的小脸蛋,弄得我“格格格”地笑个不停。等到父亲请相邻的会排八字的同族瞎子阿公给我取了一个正式名字以后,他一边用温暖的双手抱着我,沿着崎岖不平的山村曲径小路盘桓周游,并轻轻左摇右摆着逗我开心,一边嘴里反复不停地顺口哼着“阿苗乖、阿苗乖、阿苗乖……”像母亲哼唱摇篮曲一样给我催眠。
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抱着我慢慢长大,我和他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到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只要一见到他的身影,就会张开甜甜的小嘴巴,十分亲切地称呼他“阿太、阿太”。因为,我的亲阿太已过世多年,毫无印象,其实,我早就认他作嫡亲阿太了。
然而,他却极讲究分寸,从未上我们家的那张圆圆的饭桌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酒,连同他那把常年捧着的旧陶瓷茶杯,也是他从里明堂自己家里随身携带过来的,最多只是偶尔在我家的竹壳热水瓶里续一点热水而已,连我们家的灶间也很少进。我家每次临开饭前,他就静悄悄地独自一人回家生火做饭去了。
他家的屋后山坡上,有他用汗水亲手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两块面积不等手绢形状的袖珍私有地,附近还有一块一亩多巴掌大的自有毛竹山。从我三四岁起,我常常跟在他的屁股后头,耳闻目染地看他翻地、播种、施肥、割菜、摘瓜和寻笋、挖笋等,从小培养了我的劳动意识。收获的蔬菜瓜豆等他一个人吃不完,都会无偿馈赠给左邻右舍,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助人为乐的精神。
一年四季挖掘收获的冬笋、春笋和鞭笋,他一畚箕一畚箕地肩负手提着到十里外的车厩赶集,换取些许零用钱,除却油盐酱醋花销,会购买一些小糖、饼干、桃酥、香糕等之类的零食放在床头,他不时会分一半给我分享。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十分匮乏的岁月,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呀!我至今还回味无穷。后来出生的弟妹俩都没有这个福分。和我同龄的许多同伴们,每当看到村中小店柜台上整齐摆放着的各种糖果糕点,人人都会口水潺涎。
我作为家中的大孙子,小时候常常会任性耍小脾气,他看见后会出场演戏当“和事佬”。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未顺我的心,就在家里耍起了无赖,滚在地上又哭又闹。我祖母好说歹说都没用,打骂又不舍得。于是,她灵机一动,径直走到灶膛前取出一把干柴火,点燃一根火柴来吓唬我。阿太见状立即一把将我抱起,连哄带骗的一通安抚,才纾解了我偏激的情绪。
到我9岁那年,我背上新书包到惇裕堂张氏宗祠的左偏厢上小学读书。张阿太知道后,十分关心,经常到教室门窗外“探班”察看,了解打听我在校的学习情况。下课后,他还用现身说法教育和鼓励我要珍惜机会,好好读书,力争将来有一个好出息。
新学期的课本一下发,他小心翼翼地翻看着一页又一页花里花哨的图文,顿时,流露出满脸的无奈和遗憾,频频摇头。他一边翻看课本,一边对我说:他的上代坤镛公就是靠远赴慈城中小学和杭州当年的浙江政法学校读书,后来在宁波开明街开律师所搞得风生水起,名噪一方的。过去,他小时候由于家里实在太穷读不起书,也根本没有地方去读书。所以,而今他是大字不识一个,两眼一抹黑,人称“亮眼瞎子”,根本就出不了远门。同时,他打心底里羡慕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当他看到我语文、算术两门功课作业和每次考试成绩都满分时,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所崇敬的这位长辈,平时总习惯捧着那把旧陶瓷茶杯的阿太,安详地闭上了他的双眼而驾鹤西去。出殡当日,我双手捧着他的洁白牌位,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来自苹果APP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