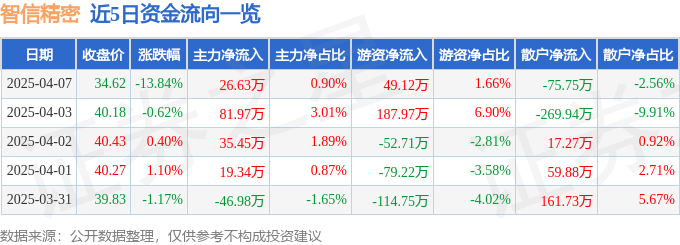埠头与集市,两者对于有船能通过的水系来说,历来都有着重合的关系。陆埠原称陆家埠,顾名思义,陆姓在此地占了头筹,于是这条兰溪流过的集市因陆家所在的埠头而从兰溪市改名为陆家埠市。改名的缘由不得而知,不过也不出两种可能,一是集市位置的移动,从原来的兰溪市集区域转向地理位置更为方便的陆家埠区域;二是因为陆姓的强势,若陆姓把此地当做集市交换的核心场所,对于参与集市的人来说,埠头集市谁家开便姓谁。似乎第一种猜想更接近现实,它同时也包含了第二种猜想中陆行渐渐强势的趋势。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地方志上也仅仅是记录了改名这一事实,至于细节并未作进一步的展开,地方志似乎是秉承了官史缺点的衣钵,自从汉书以来只记变化不体人情,与史祖司马迁的文风大相径庭,可以这么说,地方志是极难读的,尤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资料汇编,对于文献查考来说倒是不错的选择。
陆埠作为里山七二岙的汇集之所,处于四明山北麓的丘陵与平原交汇处,不仅有顺流而下河道足够宽的水势,又有纵横宁绍平原的平地优势。不过,姚江流域水系相对来说还是很发达的,这也就造成了河道之间船只运载人或货物成为运输的首选,这也是在商品经济从明朝萌芽以来,陆家埠作为里山七十二岙的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骤显,代替原来简单集市功能的兰溪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的儿童时代,差不多是1985年左右。那时候的陆埠,开始有了改革春风的迹象,同时还保留着相当多的地方传统,这些地方传统往往体现在旧房子旧街道依然如旧,街上的叫卖声还是土里的乡音,卖的东西也大多是自己产的东西,很少有专门从事贩卖的商业应为,如果时光拨回去,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纯朴的时代,纯朴中又不乏积极的生活态度。
我的外婆家,在余姚城南的乡下,田畈边的村庄叫上畈,其实那也只是个自然村,又被称作为大队,真正的行政村名叫双桥村,据说是因桥得名,奇怪的是,我的印象中再也找不出桥的摸样了,也不知桥的方位在何处,只记得有个奇怪的桥名还印在脑海中,类似乒乓的词汇结构,其(缺右脚)其(缺左脚)桥,发音也非常不可思议,叫jueg,字典上是找不着。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很多乡音与汉语普通话是对应不起来的,按照这样的说法,类似的部分词汇在民间的保留可能意味着两种可能,一是土著的发音,二来此地是非汉语普通话体系的外来移民的发音。随着汉语普通话的普及,带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将渐渐死亡,不知道这是种可惜的成就还是无奈的伤感,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后者的成分似乎占据了上风。
每次外婆家来回,都会经过陆埠最繁华的街道,现在菜场外围得两条街便是,最有名的当然是兰溪街,每当有人提起的时候总是声调略显升高,著名的陆埠豆酥糖就是生产于这条街上,一层白色的纸包着,外面印有一个小章 “陆埠豆酥糖”的字样。陆埠豆酥糖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只要你吃过你便会有印象,好吃的是粘粘的部分,略微干的时候会分成片,恼人的是粉状部分,吃得满嘴都是,所以说,只要你在家偷吃了豆酥糖,你是无法抵赖的,一看便知。
记得那个时候,每逢走亲戚,或者过年过节,都会送上糕点包,一般都是豆酥糖、红枣或者白糖,用厚厚的麻纸包起来,上面贴一张印有糕点字样的红纸,最后用线包扎好。我们最常见的偷吃方法就是从一角弄开来弄一包豆酥糖出来吃,以为大人会不知道,要是今天偷了一包明天又偷两包的话,那就比较不好了,因为那个包大多是用来串门走亲戚的时候再送出去的,等到最后一个环节停下来不再转送的时候,原来十二包都豆酥糖只剩能六七包的时候,总是会让人尴尬的,不过,谁会当着客人的面拆开客人送来的礼呢,这不符合习俗。
既然是陆家埠市,不可避免地要谈集市。先民的集市,一般都会有固定的日子,像三七市,即每月逢三逢七集市,二六市,即每月逢二逢六集市,附近几个集市一般都会把集市的时间错开,这样就便于处在几个集市区域内部有物品交换需求的村民每天都有机会参加集市。三七市、二六市镇名与集市名称同名,虽然有些过于简单,不过也比较好记,或许没有像兰溪、陆家埠这样鲜明又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名字代替也有很大关系。
从余姚过来进入里山七十二岙的汽车,如果不进入镇上,它会选择在桥头三岔路口的车站停车后从右侧岔路大路而去。陆埠车站是个普通的车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车站,建筑与内部组织我想与当时的全国各地小镇车站也没有太大区别。门口大大的深红车站字样,候车室内深红的木质长凳,穹顶柱状的售票口,这些在我们的印象中始终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陆埠似乎不仅仅是个镇,那时还是个区,区的级别比镇要高,我们宋岙村所属的洪山乡归陆埠区所辖,这大概也是2003年撤乡并镇的时候洪山乡撤销重新归属陆埠镇的原因吧。里山七十二岙,在80年代初中期几乎是村村通车的,像宋岙这么一个山顶小山村也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配备,有村汽车站、有汽车停靠的内屋、有专职司机,而且司机的态度也是出奇的好,尽量让能所有乘客上车,我记得有一年年底回家,都是靠着司机师傅的档杆站着回家的,毕竟,如果不能上自己村的车,那就要乘别村的车,似乎要退票重新买票的,而且要到就近的地方下车,这也是我有从上方到宋岙、翁岙到宋岙山路经历的原因。
私营经济兴起,加上人流外涌,像村村通大客车这样的乌托邦似的国营行为渐渐被私营的中巴车代替,甚至到了现在,不少户口数少的村庄都没有正常时刻表的中巴车通行了,对于发展这个词我们正要好好反思一下了,25年后,我们竟然不能坐专门的车回村了,回家都成了临时的出击对象,要么坐其他大村的中巴车中途下车,然后再走几公里路,或者从陆埠坐很狭窄的没有固定时刻表的小面包车回家。
这还不算最差的,自1980年宋岙村通公路,2000年左右浇上水泥路以来,按理说,路是越来越好了,交通理应越来越方便才对,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与当初花大力气以愚公移山精神修公路的先民初衷背道而驰了。村里的年轻人不愿意呆在村子里到城里打工,随着荷包是身份象征符号以后,村庄除了老人小孩留守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要致富,先修路,我倒是觉得要改成,要致富,先跑路。
对于坐车的难受程度来说,当数村里的小孩子,以前村里有自己的小学,我们都是上完小学六年级才到乡上的初中念书,现在什么样子呢,说是要提高教育质量,集中教育资源,村里的小学撤掉了,哪怕上幼儿园的孩子都要到袁马寄宿,每逢星期五下午回家、星期一上午到学校,小小的小面包车里在那两个时段是挤满了人,这个事情新闻上常有报道,完全隐患非常之严重。
陆埠镇上的故事,老人有老人的故事,新生的孩子有新的故事,只不过有些故事消逝了,有些故事却因故有了下来。我脑海中对于陆埠镇上印象最早也是最深的故事,是村里一位堂伯当船老大,因为救人而失去生命的事迹,好的事迹固然让人心热,只是这位堂伯过世后留下两个尚处儿童阶段的孩子,不得以母亲带着孩子改嫁了,嫁就嫁到了陆埠镇上的桥西。从这个故事里大人还教给我们一个道理,救人前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作为船老大,哪怕是自己谙熟游泳技术,也不能自己下水救人,只须投递过去一根划船的竹竿即可,要是你跳下水去救人,结果往往是两个人都上不来。
陆埠有一座桥,跨越兰溪把陆埠镇分成桥东桥西两个区块,桥东是老镇繁华所在,桥西则像是镇上的郊区,至少当时是这么看的。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过眼回忆里,桥头的照相馆确实带给了大家不少过去的照片,使得能让现在的人们通过老照片这个线索来追忆过往。“梭糊货郎桥,桥头照相馆”,陆埠人谁能不晓?
在我爷爷生活的年代里,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几乎村村都通公路,实际上,陆埠进里山七十二岙是没有公路的,只有一条沿着兰溪而上的沿溪小路,小路随着溪流的蜿蜒而曲折,随着上游支流的散开而分岔。爷爷担着山货(主要是成捆的毛竹)沿着缘溪的小路走过20几里的山路到达陆埠,由于不能错过赶集时间,天蒙蒙亮就要出发了,带上干粮与水壶直奔集市而去。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兄弟俩上番岗山人砍柴,由于肩膀嫩,母亲只给我们每人10来斤重的担子挑,即使这样,5、6里的山路我也是两头摇摇晃晃,中间要放很多次才能到家。回忆过去的苦日子,想想现在工作生活都不用啥体力,自然会觉得幸福太多,只是上一辈传下来的吃苦耐牢的精神始终存在心里,虽然有时候也会忘却,但每当陷入困境总会有遗传下来的精神支撑着自己,不断勉励自己来走过困难的人生低谷阶段。
“侬到阿里起”,“偶到陆埠起”,这样的对话在出门的路上常会碰到,尤其是在出村的车上。对于村里来说,陆埠已经是很繁华的地方,像我母亲是从余姚城区周边嫁到山里来的,在村里人看来是见过市面的人,加上我母亲又是小学毕业,在村里媳妇群里也可算是非常难得,要是碰上邻居来了上海的客人,那简直都把来客当成是天外飞仙。
每逢集市,陆埠镇上总是热闹异常,人流多得似乎都要挨着慢行才能通过大街,像我小时候个字只及大人腰部的小不点那更是眼不能及、唤不能应。小巷子里的石板路和两旁的木质旧房,是典型的江南古镇风格,加上美丽的兰溪水流过,俨然画里风景,只是陆埠这个地方经济起步早,我们知道,经济起步早的地方往往马路、建筑破坏得也最厉害,要不然,江南古镇的广告又会多一则陆埠的。
大街两旁都是山民的货物,有竹椅、扫把、淘箩、饭篮、竹席等竹子做的日常用品,也会有平原地区农民自己培育的番薯苗、菜秧等山民采购的东西。兰溪埠头停满了乌篷船,一船船的大白菜、土瓷器搁在船上叫卖,船主一般只是叫卖,东西是不搬出船的,除非交易完成,这样做也是为行船越点叫卖方便。陆埠镇是个山民与平原农民物物交换的理想场所,虽然中间会涉及货币,不过谁会空手而不采购些东西回家呢?
陆埠桥上看集市也是别有味道,这座位于兰溪转弯处的大桥也是看美景的所在。兰溪水清清流淌,倒影着看风景人的身影,水里成群的溪鱼流过,时动时静,似乎人唤它的它们是动的,不唤的时候它们又是安静的。溪鱼,我们叫它“畅丝”(谐音),非常鲜美,哪怕是小小的鱼刺,吃在嘴里也与河鱼不同。
时过境迁,陆埠镇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毕竟作为货物集散地的枢纽功能已经不再,只是还留有曾经的故事与传说。兰溪水依然流淌着,大桥依然屹立着,闭上眼我又看到了你,睁开眼睛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回忆。美丽的陆埠,美丽的镇上,古镇的色彩已经不在,不变的是群山流下的溪水汇聚成的兰溪,若溪若江的兰溪水,似乎还在诉说着过去,诉述着我们祖上的回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地方志上也仅仅是记录了改名这一事实,至于细节并未作进一步的展开,地方志似乎是秉承了官史缺点的衣钵,自从汉书以来只记变化不体人情,与史祖司马迁的文风大相径庭,可以这么说,地方志是极难读的,尤其说是史书,不如说是资料汇编,对于文献查考来说倒是不错的选择。
陆埠作为里山七二岙的汇集之所,处于四明山北麓的丘陵与平原交汇处,不仅有顺流而下河道足够宽的水势,又有纵横宁绍平原的平地优势。不过,姚江流域水系相对来说还是很发达的,这也就造成了河道之间船只运载人或货物成为运输的首选,这也是在商品经济从明朝萌芽以来,陆家埠作为里山七十二岙的商品集散地的功能骤显,代替原来简单集市功能的兰溪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的儿童时代,差不多是1985年左右。那时候的陆埠,开始有了改革春风的迹象,同时还保留着相当多的地方传统,这些地方传统往往体现在旧房子旧街道依然如旧,街上的叫卖声还是土里的乡音,卖的东西也大多是自己产的东西,很少有专门从事贩卖的商业应为,如果时光拨回去,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纯朴的时代,纯朴中又不乏积极的生活态度。
我的外婆家,在余姚城南的乡下,田畈边的村庄叫上畈,其实那也只是个自然村,又被称作为大队,真正的行政村名叫双桥村,据说是因桥得名,奇怪的是,我的印象中再也找不出桥的摸样了,也不知桥的方位在何处,只记得有个奇怪的桥名还印在脑海中,类似乒乓的词汇结构,其(缺右脚)其(缺左脚)桥,发音也非常不可思议,叫jueg,字典上是找不着。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很多乡音与汉语普通话是对应不起来的,按照这样的说法,类似的部分词汇在民间的保留可能意味着两种可能,一是土著的发音,二来此地是非汉语普通话体系的外来移民的发音。随着汉语普通话的普及,带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将渐渐死亡,不知道这是种可惜的成就还是无奈的伤感,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后者的成分似乎占据了上风。
每次外婆家来回,都会经过陆埠最繁华的街道,现在菜场外围得两条街便是,最有名的当然是兰溪街,每当有人提起的时候总是声调略显升高,著名的陆埠豆酥糖就是生产于这条街上,一层白色的纸包着,外面印有一个小章 “陆埠豆酥糖”的字样。陆埠豆酥糖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只要你吃过你便会有印象,好吃的是粘粘的部分,略微干的时候会分成片,恼人的是粉状部分,吃得满嘴都是,所以说,只要你在家偷吃了豆酥糖,你是无法抵赖的,一看便知。
记得那个时候,每逢走亲戚,或者过年过节,都会送上糕点包,一般都是豆酥糖、红枣或者白糖,用厚厚的麻纸包起来,上面贴一张印有糕点字样的红纸,最后用线包扎好。我们最常见的偷吃方法就是从一角弄开来弄一包豆酥糖出来吃,以为大人会不知道,要是今天偷了一包明天又偷两包的话,那就比较不好了,因为那个包大多是用来串门走亲戚的时候再送出去的,等到最后一个环节停下来不再转送的时候,原来十二包都豆酥糖只剩能六七包的时候,总是会让人尴尬的,不过,谁会当着客人的面拆开客人送来的礼呢,这不符合习俗。
既然是陆家埠市,不可避免地要谈集市。先民的集市,一般都会有固定的日子,像三七市,即每月逢三逢七集市,二六市,即每月逢二逢六集市,附近几个集市一般都会把集市的时间错开,这样就便于处在几个集市区域内部有物品交换需求的村民每天都有机会参加集市。三七市、二六市镇名与集市名称同名,虽然有些过于简单,不过也比较好记,或许没有像兰溪、陆家埠这样鲜明又被大家普遍接受的名字代替也有很大关系。
从余姚过来进入里山七十二岙的汽车,如果不进入镇上,它会选择在桥头三岔路口的车站停车后从右侧岔路大路而去。陆埠车站是个普通的车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车站,建筑与内部组织我想与当时的全国各地小镇车站也没有太大区别。门口大大的深红车站字样,候车室内深红的木质长凳,穹顶柱状的售票口,这些在我们的印象中始终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陆埠似乎不仅仅是个镇,那时还是个区,区的级别比镇要高,我们宋岙村所属的洪山乡归陆埠区所辖,这大概也是2003年撤乡并镇的时候洪山乡撤销重新归属陆埠镇的原因吧。里山七十二岙,在80年代初中期几乎是村村通车的,像宋岙这么一个山顶小山村也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配备,有村汽车站、有汽车停靠的内屋、有专职司机,而且司机的态度也是出奇的好,尽量让能所有乘客上车,我记得有一年年底回家,都是靠着司机师傅的档杆站着回家的,毕竟,如果不能上自己村的车,那就要乘别村的车,似乎要退票重新买票的,而且要到就近的地方下车,这也是我有从上方到宋岙、翁岙到宋岙山路经历的原因。
私营经济兴起,加上人流外涌,像村村通大客车这样的乌托邦似的国营行为渐渐被私营的中巴车代替,甚至到了现在,不少户口数少的村庄都没有正常时刻表的中巴车通行了,对于发展这个词我们正要好好反思一下了,25年后,我们竟然不能坐专门的车回村了,回家都成了临时的出击对象,要么坐其他大村的中巴车中途下车,然后再走几公里路,或者从陆埠坐很狭窄的没有固定时刻表的小面包车回家。
这还不算最差的,自1980年宋岙村通公路,2000年左右浇上水泥路以来,按理说,路是越来越好了,交通理应越来越方便才对,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与当初花大力气以愚公移山精神修公路的先民初衷背道而驰了。村里的年轻人不愿意呆在村子里到城里打工,随着荷包是身份象征符号以后,村庄除了老人小孩留守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要致富,先修路,我倒是觉得要改成,要致富,先跑路。
对于坐车的难受程度来说,当数村里的小孩子,以前村里有自己的小学,我们都是上完小学六年级才到乡上的初中念书,现在什么样子呢,说是要提高教育质量,集中教育资源,村里的小学撤掉了,哪怕上幼儿园的孩子都要到袁马寄宿,每逢星期五下午回家、星期一上午到学校,小小的小面包车里在那两个时段是挤满了人,这个事情新闻上常有报道,完全隐患非常之严重。
陆埠镇上的故事,老人有老人的故事,新生的孩子有新的故事,只不过有些故事消逝了,有些故事却因故有了下来。我脑海中对于陆埠镇上印象最早也是最深的故事,是村里一位堂伯当船老大,因为救人而失去生命的事迹,好的事迹固然让人心热,只是这位堂伯过世后留下两个尚处儿童阶段的孩子,不得以母亲带着孩子改嫁了,嫁就嫁到了陆埠镇上的桥西。从这个故事里大人还教给我们一个道理,救人前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作为船老大,哪怕是自己谙熟游泳技术,也不能自己下水救人,只须投递过去一根划船的竹竿即可,要是你跳下水去救人,结果往往是两个人都上不来。
陆埠有一座桥,跨越兰溪把陆埠镇分成桥东桥西两个区块,桥东是老镇繁华所在,桥西则像是镇上的郊区,至少当时是这么看的。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过眼回忆里,桥头的照相馆确实带给了大家不少过去的照片,使得能让现在的人们通过老照片这个线索来追忆过往。“梭糊货郎桥,桥头照相馆”,陆埠人谁能不晓?
在我爷爷生活的年代里,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几乎村村都通公路,实际上,陆埠进里山七十二岙是没有公路的,只有一条沿着兰溪而上的沿溪小路,小路随着溪流的蜿蜒而曲折,随着上游支流的散开而分岔。爷爷担着山货(主要是成捆的毛竹)沿着缘溪的小路走过20几里的山路到达陆埠,由于不能错过赶集时间,天蒙蒙亮就要出发了,带上干粮与水壶直奔集市而去。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兄弟俩上番岗山人砍柴,由于肩膀嫩,母亲只给我们每人10来斤重的担子挑,即使这样,5、6里的山路我也是两头摇摇晃晃,中间要放很多次才能到家。回忆过去的苦日子,想想现在工作生活都不用啥体力,自然会觉得幸福太多,只是上一辈传下来的吃苦耐牢的精神始终存在心里,虽然有时候也会忘却,但每当陷入困境总会有遗传下来的精神支撑着自己,不断勉励自己来走过困难的人生低谷阶段。
“侬到阿里起”,“偶到陆埠起”,这样的对话在出门的路上常会碰到,尤其是在出村的车上。对于村里来说,陆埠已经是很繁华的地方,像我母亲是从余姚城区周边嫁到山里来的,在村里人看来是见过市面的人,加上我母亲又是小学毕业,在村里媳妇群里也可算是非常难得,要是碰上邻居来了上海的客人,那简直都把来客当成是天外飞仙。
每逢集市,陆埠镇上总是热闹异常,人流多得似乎都要挨着慢行才能通过大街,像我小时候个字只及大人腰部的小不点那更是眼不能及、唤不能应。小巷子里的石板路和两旁的木质旧房,是典型的江南古镇风格,加上美丽的兰溪水流过,俨然画里风景,只是陆埠这个地方经济起步早,我们知道,经济起步早的地方往往马路、建筑破坏得也最厉害,要不然,江南古镇的广告又会多一则陆埠的。
大街两旁都是山民的货物,有竹椅、扫把、淘箩、饭篮、竹席等竹子做的日常用品,也会有平原地区农民自己培育的番薯苗、菜秧等山民采购的东西。兰溪埠头停满了乌篷船,一船船的大白菜、土瓷器搁在船上叫卖,船主一般只是叫卖,东西是不搬出船的,除非交易完成,这样做也是为行船越点叫卖方便。陆埠镇是个山民与平原农民物物交换的理想场所,虽然中间会涉及货币,不过谁会空手而不采购些东西回家呢?
陆埠桥上看集市也是别有味道,这座位于兰溪转弯处的大桥也是看美景的所在。兰溪水清清流淌,倒影着看风景人的身影,水里成群的溪鱼流过,时动时静,似乎人唤它的它们是动的,不唤的时候它们又是安静的。溪鱼,我们叫它“畅丝”(谐音),非常鲜美,哪怕是小小的鱼刺,吃在嘴里也与河鱼不同。
时过境迁,陆埠镇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毕竟作为货物集散地的枢纽功能已经不再,只是还留有曾经的故事与传说。兰溪水依然流淌着,大桥依然屹立着,闭上眼我又看到了你,睁开眼睛所有一切都变成了回忆。美丽的陆埠,美丽的镇上,古镇的色彩已经不在,不变的是群山流下的溪水汇聚成的兰溪,若溪若江的兰溪水,似乎还在诉说着过去,诉述着我们祖上的回忆。